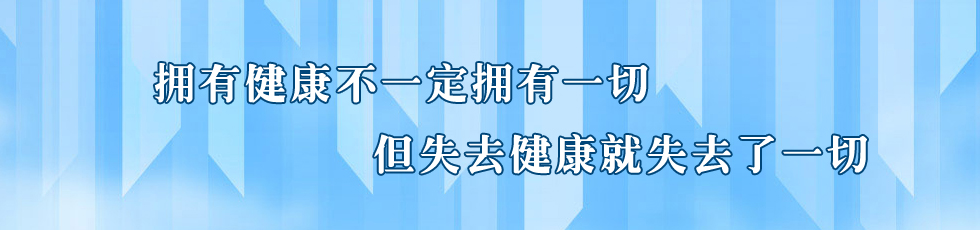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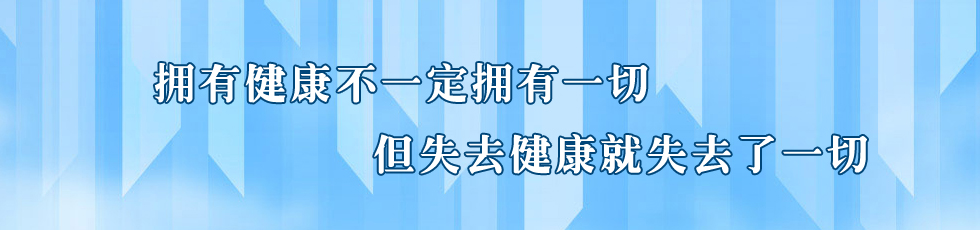
“乡愁·林甸记忆”征文——父亲的肩膀作者陈清正 人说,子欲孝则亲不待。这句话,我有着很深的体会。我的父亲一生坎坎坷坷,我们还没来得及孝顺他老人家,他就匆匆地离开了我们,想来已经快二十年了。 二十年来,父亲的音容笑貌,始终浮现在我的心中。每当想起他老人家,我就觉得心里有很多的内疚和遗憾。 我的父亲应该算是第一批从山东来林甸的垦荒队员,来到林甸不久,父亲就得了急性阑尾炎。乡亲们用担架抬着他,徒步几十里,把他医院,上医院无论是医术,还是设备,都还相当的简陋。医院以后,他的阑尾已经化脓了,医院诊断后,决定立即手术。按说阑尾切除后,就应该痊愈了,可是,我父亲半个月后,刀口就是不愈合,无奈转院至齐齐哈尔。在那里,又住院治疗一个多月,刀口仍然没有愈合,两个月后,转回山东老家继续康复。 直到半年以后,父亲的刀口突然又肿了起来,刀口处流出了很多的脓液,他无奈医院治疗。没有多久,从刀口处长出一个拇指大的东西,护士给他换药时,用镊子把它拔了出来,原来,那是做阑尾切除手术时,落在腹腔内的一块纱布。打那以后,伤口逐渐地愈合了,父亲就没有回来。到了一九六四年,由于我母亲有病,再加上巨浪牧场招工,我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又返回了林甸,因为晚来了一个月,巨浪牧场招工已经结束了,我们家就落户在林甸原黎明乡的东方红大队四队,也就是新村四号。 父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,少年读过私塾。他十六岁那年,正是学业进步的大好时光,然而,命运却阻止了他奋进的脚步。我的爷爷和奶奶得了重病,父亲因此放弃了学业,拾起了家里的重担。据他说,我的爷爷奶奶有病以后,他不惜一切到处求医买药,家里的东西几乎卖光。那个时候,没有什么代步工具,几乎都是步行,他早晨出去,回来的时候,都要半夜了。 有一次,他去二十里地外的一个药铺,给爷爷抓药,回来的时候,已近三更。漆黑的夜晚,他一个人急匆匆地走着。突然,在他的前边,出现了一个黑色的、很高的东西,上连着天,下接着地,我父亲走,那个东西就往前走,我父亲停下,它也停下,莫非这世界上真的有鬼吗?幼小的父亲吓出了一身冷汗。那个地方,前不着村,后不着店,退也无处退。父亲就豁出去了,大踏步地朝着黑色的东西走去。 走了一阵子,那个黑色的东西就逐渐地变矮、变短,后来,就消失了。原来,他面前是一条笔直的大路,那种黑色的东西,只是一种错误的视觉现象。 还有一次,也是深夜,那时候,我老家那个地方,不像现在村子密集,一个接一个的,而是很远也看不到一个村子,当他走到一片荒郊的时候,忽然,从路边起来了一团火,那火通亮,沿着我父亲回家的方向,不紧不慢地缓缓前行。当时,把我父亲吓得胆突突地前行着,过了很久,那团火才消失。当那团火消失的时候,他才发现已经快到自己的家了。 我父亲后来解释说,这件事情,在他的脑海里始终是个疑团,自己很多年以后,看一本科技书时才找到答案,那团火就是传说中的磷火,是一种自然现象。他说,虽然没有迷信,总觉得那天好怪,好像磷火也知道这个幼小的孩子是为了给父母买药才走夜路的,它的适时出现,就是为了给我父亲引路回家的。 尽管父亲百般求医找药,但还是没有治好我爷爷奶奶的病,那年的秋天,爷爷奶奶离开了人间。 十六岁的父亲和我姑姑挑起了照顾五个叔叔的重担,我的六叔当时才六岁。我爷爷奶奶去世前,就已经给我姑姑找了婆家,并且确定了结婚的日子。转过年来,我的四叔染上了伤寒,姑姑出嫁的那一天,我的四叔去世了。又过了一年,我的五叔和六叔也相继早逝。 我父亲带着我的二叔和三叔,艰难地生活着。 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后,像做父母一样,照顾着我的二叔和三叔,后来,他们也都如愿地成了家。 本来,父亲应该缓口气过一段幸福的小日子了,正在这时,我的母亲由于过度劳累,得了严重的肺结核,这一病就是十五年。 父亲既要去生产队干活,又要照顾我生病的母亲,还要照顾孩子。屋漏偏遇连夜雨,命运并没有因此放开父亲,仍然无情的摧残着他。在我之后,先后死掉了一个弟弟、三个妹妹,三个妹妹死的时候都是两三岁,惟有我二弟弟死的时候六岁,他们各个聪明伶俐。对我父亲打击最大的,是我的那个弟弟,他长得活泼可爱,聪明帅气,因为发烧,父亲背着他去卫生所打针,不幸死于医疗事故,我父亲几乎是绝望了,险些疯了。 不过,他还是顽强地站了起来,勇敢地面对生活。 我父亲惟一的成就感,就是看着我们一天天地长大。我小的时候,父亲总是喜欢背着我到大门下边和乡亲们聊天。记得我刚记事儿的时候,他还背着我去很远的一个村子看电影,那是我第一次看电影,电影画面中的特写由远及近,给我吓得哇哇直哭,父亲只好把我背了回来,搅得他也没看成电影。 我六七岁以前,我只要生病了,我父亲都会医院看病,所以,在我的童年记忆里,父亲的肩膀是那样的宽阔,那样的结实。每当他干活回来,他坐在炕沿上吸烟,我总是靠在他的肩膀上。现在想起来,那时,真好,真的温暖。 我父亲十分重视我的学业,不管他多累、多忙,只要看着我写作业,他从来不支使我去干活。我每天上学回来,他都要问一遍在学校里一天的情况,直到我初中毕业。 上小学的时候,每逢晚饭,父亲都会问我一些生字,他一边吃饭,一边看着我用筷子给他比划,答对了,他就笑呵呵的,答错了他就立即纠正,还经常地考我一些同音字、生词和造句,这使得我在小学就打下了很好的语文基础。我父亲是我最好的小学老师。 可能也是为了让我学习好,我父亲很少把那些说话粗鲁、满嘴脏话的人带到家里来,倒是经常地约一位被大家称呼为“李先生”的李大爷来我家聊天。李先生曾经给国民党大将王耀武当过秘书,有着十分优厚的文化功底。冬天,父亲烧着干锅,屋里暖烘烘的,他俩抽着烟,议论着过去上私塾时学的一些东西。他们议论《三字经》、议论《论语》等一些国学文章和历史经典,我就趴在被窝里,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们的讲述。这些不经意间接受的知识,对于后来我的做人、做事以及文化学习,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父亲教育孩子,不仅是言传,更注重于身教。他的举止行为总是奉行着自己的做人原则,让孩子知道什么是对与错,什么是是与非。我家住的两间破房子,外屋靠近北墙的一根檩子断了,好心的朋友劝我父亲,生产队院子里刚从林甸县城拉回来很多木头,根本没有详细数字,晚上没人的时候,你扛回来一根,别人也不会发现,明天我们几个帮着你把檩子换上。 说实在的,乡亲们真是好心,他们知道我家买不起檩子,才出此下策。可是,我父亲坚定地认为这就是偷!他告诉我,这种不仁不义的事情,咱坚决不能做!他没有去“偷”,在邻居家找了一根很细的木头,立起来把那根断了的檩子给支上了,一直到我长大以后,我花钱买了木头,才将那根断了的檩子换了下来。 那些年,我家相当的困难。有时,玉米面的饼子窝头都接不上捻,青黄不接的时候,母亲就去园田地里扒一些土豆子回来打接济,很少吃到面食,尤其是我父亲,一年四季都很少吃一口面食和炒菜。 那年头,食用油靠供应,吃的粮食由队里分,每个人每月才供应二两食用油,每年队里每人仅能分到小麦三十到五十斤,磨成面粉也就是有个二十到四十斤那样,父亲舍不得吃,省下来营养我生病的母亲和我们。 我清楚地记得,那时候生产队打羊草,由于活很累,队里集体起伙,吃些面食,有时晚上这一顿,父亲把分得的馒头舍不得吃,放在怀里揣回来,回家给我吃,还说,我不喜欢吃馒头,喜欢吃大饼子。直到若干年以后,我父亲才说心里话,他最不喜欢吃的就是玉米面的大饼子。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,我父亲没有穿过新衣服,他的衣服都是补丁摞着补丁,一件棉袄穿了很多年。我三叔家我弟弟清林曾经写过一篇文章,在《黑龙江日报》上发表,题目就叫《大爷的棉袄》,那件破棉袄,几乎成了我父亲一生标志性的衣服。 我父亲还不到五十岁,我母亲就去世了,他领着我和我弟弟艰难的生活着,母亲去世的时候,为了给她治病,我家还欠了很多外债,直到我结婚时,还没有还清。 我父亲嫉恶如仇,爱憎分明,他见了不忠不孝的人、那些见利忘义的人,很少与他们说话。但是,我当了干部、尤其是当了领导以后,他就像换了一个人,不管见了什么样的人,他都主动地面带微笑和人家打招呼,他说,当干部、当领导,我们不能让人家说咱有架子,相反,我们更要谦虚、谨慎,和乡亲们打成一片。 我当了干部,有了稳定工作,我弟弟在部队服役,学了医生,本来日子已经好起来了,就在这时,我父亲被查出了胃癌晚期。我接过诊断书,眼睛都模糊了,我不敢和他说细情,把医生开的抗癌药物的商标揭了下来。我父亲有文化,他虽然没有看到诊断书,但是他什么都明白了。 当他知道自己得了绝症以后,就提出不再治疗了。他说,人总有一死,我这一生,活的不亏心,有你们哥俩和你们的媳妇这样懂事,我就知足了。在我再三的劝说下,他才答应了我给他治病的要求。 那以后,他戒掉了烟瘾,每天早晨要走好远,锻炼身体,他那瘦削的身体,高挑的体型,挺拔的腰板,健硕的步伐,从后面看,谁都看不出他是个癌症患者。他以顽强的毅力,向上苍乞讨着生命的延续,我多么期盼在他的身上会出现奇迹啊。 然而,命运并没有开恩于这个可怜的老人,父亲最后还是无奈地倒下了。躺在床上,他和我说了很多很多,并让我拿来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,他用坚强的意志,凭着他的记忆,给我写了一本家谱,这是我父亲的绝笔之作。 最后,我父亲说,这是我最后和你们说话了,我已经没有力气了。从此,父亲再也没有说话,他临咽气的时候,我感觉事情不好,就抓住他的手,大声地呼喊他,又把他喊了回来。我问他你现在明白吗?如果明白,你攥一下我的手! 我明显地感觉到,父亲那只大手,已经没了温度,但是,他还是轻轻地握了我的手!之后,他就走了...... 父亲去世了,他原来那个坚实的肩膀,变得那样的单薄。 伟大的父亲,我要对你说,你经历了少年丧父、壮年丧子、中年丧妻的人间不幸,你没有趴下,像大山一样站着,任何困难都被你踩在脚下,你是巨人,用你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家,扛起了你的责任!我们永远地怀念您,如果有来世,您还做我的父亲吧! 林甸,我的青葱学生时代(“乡愁·林甸记忆”征文) 更多好文,敬请期待 作者简介:陈清正,男,年3月生,祖籍山东泰安,中共党员,做过农民,当过村团支部书记,考上干部后曾任党委秘书、党委宣传委员、原隆山乡乡长助理、副乡长、党委副书记,原黎明乡党委副书记,林甸县农经总站站长。 直接点击阅读 我的父亲在林甸(“乡愁·林甸记忆”征文) 那些年,爸爸的单车(“乡愁·林甸记忆”征文) 父亲的牵挂(“乡愁·林甸记忆”征文) 家园(“乡愁·林甸记忆”征文) 林甸,那些光阴的故事(“乡愁·林甸记忆”征文) 王鹏程的写意世界 扬起文学的帆(“乡愁·林甸记忆”征文) 林甸乡村工作记忆点滴(“乡愁·林甸记忆”征文) 那些年,睡在通铺的兄弟(“乡愁·林甸记忆”征文) 说说我的婆婆(“乡愁·林甸记忆”征文) 老街风景(“乡愁·林甸记忆”征文) 马车时代(“乡愁·林甸记忆”征文) 老垦荒队员的林甸记忆(“乡愁·林甸记忆”征文) 西门外也有个北大坑(“乡愁·林甸记忆”征文) 从林甸走向世界的剪纸艺术大师(五湖四海林甸人之刘延山) 我要谈谈理想(“乡愁·林甸记忆”征文) 回忆父亲(“乡愁·林甸记忆”征文) 湿地“鸟痴”吴志林:他走进了一个灵性的世界 刷爆朋友圈,“鸟叔”吴志林的拍摄现场太震撼 我的父老乡亲(“乡愁·林甸记忆”征文) 留住老柳,记住乡愁(“乡愁·林甸记忆”征文) 给母亲画素描(“乡愁·林甸记忆”征文) 故乡,我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