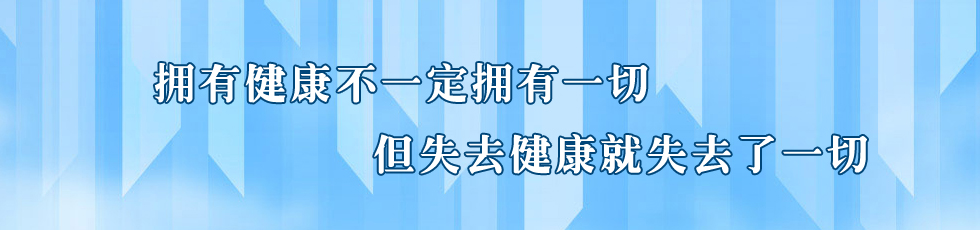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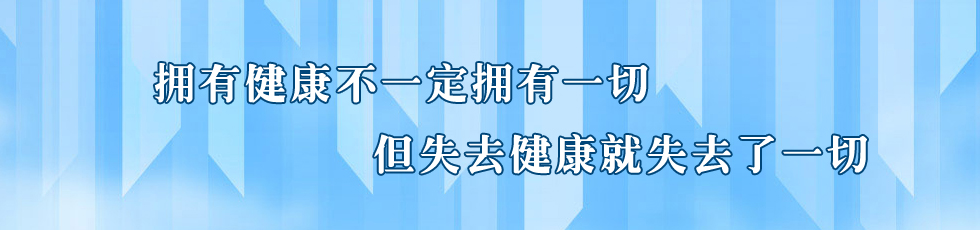
她不怕独处,不惧孤单,男人和爱情,有便有,没有便没有,她自有浑然忘我的一片天地。就像一些练功得道之人,自身和外界可以完成能量的交换,没有那要死要活、欲仙欲死的男女之情,也一样做到雍容、平和、宁静,不带火气,不裸露,永远是男人心目中的春城柳。 张充和:和爱好在一起,就不怕人生寂寞 作者 江泓 一年前的夏天,充和先生去世了,据说是在睡梦中平静地离去,并无痛苦。一定的,她一定是这样善终的。也许,年前那一天,她的降临并没有给家人带来喜悦,上头已经有三个姐姐,全家人都眼巴巴盼着来个男娃,连算命的都说这回没错,各种贺喜已经准备停当。她的呱呱坠地令张家失望了,报喜的、贺喜的都哑了声音。八个月的时候,充和由叔祖母收养,离开上海,来到合肥老家。这样的安排也说不定是命运的垂青,充和的叔祖母是李鸿章的侄女,成年后又嫁入合肥和李鸿章一样的大家族张树声家。信佛之人,法名“识修”——认识和修行。叔祖母很爱充和,对她要求也很严,比如规定她坐立行走时不能显出慵懒之态,在长辈面前保持恭敬,不许插话等等。但严格并不僵化,不失自由。她不强迫充和信佛,甚至不要求她吃素。前后请了几位家庭教师,最后才确定了山东的考古学家朱谟钦。当时一般仆人的工钱是一年20银元,叔祖母开给朱老师银元。充和每天(十天才休息半天)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,除去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,一直跟着老师读书、写字。每天八小时,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就是这样打下的。 充和16岁回到苏州大家庭,比不上几个姐姐的眼界和时尚,也略显土气,她甚至把空中飞过的飞机误认为巨大的风筝。可是姐姐们没一个敢小觑她,还公认她的诗词最好,城里长大的孩子再好的诗句都在旧书里隐约可见出处,充和的诗句却是在自然里发芽,带着晨露的,小孩子也心生敬意,分得出强弱。 父亲和几个姐姐都喜欢唱昆曲,充和一听之下倍感亲切。原来叔祖公是一位不慕功名、性情散淡之人,不爱读考试的八股,喜爱捧读佛教经典、小说诗词之类的别人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书,去世之后这些书就摆在书房里。充和稍大一点时,时常翻看,家人唱的昆曲大多是早在书房里看过的那些戏文,故人重逢的喜悦和亲切让她痴迷上了昆曲,一迷就是一生。像她的叔祖公一样,充和身上极少有现实功利心。她喜欢诗词、昆曲、书法、绘画,那样的喜欢完全来自内心的渴求和需要,不同于三位姐姐,她毫不在乎别人的掌声和赞扬。 “她们喜欢登台表演,面对观众;我却习惯不受打扰,做自己的事。”她说她一辈子都是在玩,玩书法、玩昆曲、玩诗词,不需要围观和掌声的玩,真正的乐在其中。有一次,她和元和演了一出《惊梦》,艺惊四座,有名角要求跟她再演这一曲目,她却不肯同意,怕别人会据此跟元和相比较,她觉得舞台背后的名利之争太累、太无聊,唯恐避之不及。汪曾祺曾经在一篇回忆西南联大生活、题为《晚翠园曲会》的文章里写到张充和:“有一个人,没有跟我们一起拍过曲子,也没有参加过同期,但是她的唱法却在曲社中产生很大的影响”,“她唱得非常讲究,运字行腔,精微细致,真是‘水磨腔’。我们唱的‘思凡’‘学堂’‘瑶台’,都是用的她的唱法(她灌过几张唱片)。她唱的‘受吐’,娇慵醉媚,若不胜情,难可比拟。”“我写东西留不住。谁碰上就拿去发表了。”一般文章在写张充和的时候,会这样引用老太太的一句笑语,其实原话是:“我写东西就是随地吐痰,留不住。谁碰上就拿去发表了。”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把“就是随地吐痰”这个比方抹掉了,也许觉得不雅,觉得跟老太太大家闺秀的身份不符合,其实,恰恰是这句话让我们嗅到了她掩不住的真性情。 张岱《陶庵梦忆》云:“人无癖,不可与交,以其无深情也。”真正有癖好的人都会有体会,当自己画了一幅画,写了一幅字,或者唱了一首歌,那感觉就像出了一身汗,洗了个热水澡,或者就像老太太所说,吐了一口痰,甚至像出了一次恭,好像越发不雅了,可确实有着这样宣泄和淋漓的快感,大雅和大俗本来就是相通的。充和一生所做的纯粹是为了愉悦自己,为了“吐口痰”的舒畅,写字、画画、唱曲……她从小几乎没有同龄玩伴,是这些爱好陪她长大,给了她快乐、宁静和内心笃定。 17岁,她随三姐张兆和、三姐夫沈从文来到北京,准备报考北大,为了避嫌特意用了假名“张璇”。考数学那天,家人为她准备圆规、三角尺之类的用具,她冷静地拒绝,说自己完全用不上。果然她很清爽地考了个大鸭蛋,中文也很清爽——得了满分。考试委员会惜才心切,想办法破例录取了这位女生进入中文系,进校之后,她并没有认为北大有多么了不起,尽管胡适和钱穆教思想史,冯友兰教哲学,闻一多教古代文学,刘文典教六朝和唐宋诗。她也觉得无所谓,感觉学校无法静心向学,“有好多我不了解的活动,像政治集会、共产党读书会等”,没多久她就借口肺结核办了退学。多年之后,因为在书法和昆曲方面的造诣,这位北大的肄业生又被请去教授昆曲和书法。这让我想起另一位老太太的故事。说一位老太太申请美国居住权,对方问她有何特长,她拿出一把剪刀、一张红纸,一阵眼花缭乱、纸片翻飞之后,栩栩如生的动物造型跃然纸上,让签证官叹为观止,利索地盖章。一招鲜,天下先,老理没错。 充和就是觉得和自己的爱好在一起最舒服,每天快快乐乐地习字、画画、唱曲,偶尔也跟同好者玩,更多的是一个人体会、练习。她终生保留每天临帖三个小时的习惯,说是“玩”,在别人看来也算是吃得苦中苦了,不过“玩”的人因为喜欢,因为兴趣,感受到的就是快乐和享受。“我想人有了兴趣,才会有那份责任,想要做好。”充和甚至把这种兴趣比作宗教:“无论学什么东西,没有宗教式的观念,无法学好。我对书法、昆曲、诗词都有这份宗教般的热爱。”充和无论走到哪里都带本字帖,她说:“书法是一门艺术。不练字就无法画画,不读诗词就不会喜爱昆曲。都与修养有关,就是养性。比如心情烦,什么都不想做,我还可以写字。”抗战时期,警报声中,她也不停地书写。“防空洞就在我桌子旁边,空袭警报拉响后,人随时可以下去。那时候什么事情都做不了,我就练习小楷。”这样的人是强大的,因为她的内心有所寄托,自身形成了一个小宇宙,不会轻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影响。看到过充和一张照片,年轻的充和身着一件素朴的旗袍,梳着两根麻花辫,随意坐在蒲团上,倚靠着四个煤油桶搭起的木板。那是她漂泊在云南呈贡时的简陋书桌,她就在这里就着如豆的煤油灯,看书、习字。说实话,充和算不上多么漂亮,可是疏朗、宁静的气质造就了她的美,让人不由心向往之。当时是抗战时期,充和随同姐姐兆和、姐夫沈从文在西南联大,这房间是姐夫在呈贡小镇租下的,沈从文把三间房给自己家人住,两间给画家朋友住,还有六个小房间给充和其他亲友住。充和就是在她住的房间留影的,那里本来是个小佛堂,充和喜欢,就搬了进去。因为她会吹笛子,结果弹琵琶、弹古筝的闻声而来,音乐爱好者、诗人、书法家也闻声而来,大家喜欢聚集到她的小房间,喜欢她那里的氛围和气息。 充和一直不喜欢热闹,远离政治,她的重大抉择,比如确定结婚对象和远赴他乡,都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做出的,她要的是宁静的田园牧歌式的古典生活。本来并不急于结婚,叔祖母在合肥给她留有一笔田产,因此她不会因为经济窘迫考虑嫁人,再说她喜欢自由自在,不必在意社会对已婚妇女的期待和约束,也没有那么多烦琐庸俗的烦恼。虽然有不少文人雅士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,却没有一个能真正打动她的芳心。年11月,北平快解放了。张充和知道自己是一个老式文人,不如三姐兆和,反而和姐夫沈从文相似,不太能像“弹性大,适应力强”的人,很难适应即将开始的新生活。于是,34岁的她为自己选择了婚姻,也选择了自己的下半生。进入法眼的是个外国人,叫傅汉思,出身于德国的犹太人知识分子家庭,有西班牙文学学位,也精通德、法、英、意大利文学。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,也希望寻觅东方奇遇,傅汉思来到中国,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。 结婚后,年1月,充和在上海搭船前往美国,除了几件换洗衣物,她只带着一方古砚、几支毛笔和一盒五百多年的古墨…… 一个爱笔砚、不爱金银的女人,是一个真正能找到并享受自我乐趣的女人,她不怕独处,不惧孤单,男人和爱情,有便有,没有便没有,她自有浑然忘我的一片天地。就像一些练功得道之人,自身和外界可以完成能量的交换,没有那要死要活、欲仙欲死的男女之情,也一样做到雍容、平和、宁静,不带火气,不裸露,永远是男人心目中的春城柳。这样淡淡的女人,其实更吸引人,更有迷人的魅力。充和与傅汉思之间的爱情也许没有过分炙热燃烧过,可是那样的温情也许更加恒久,淡淡的,一直温暖着彼此的人生。就在结婚52年的新千年,一位美国学生,为充和出版了一本名为《桃花鱼》的诗词集,汉英对照,译文就是老伴傅汉思翻译的。那本书只印了册,宣纸印刷,手工线装,古色古香,想象两位老人珠联璧合的生活,夫复何求? 很长一段时间,充和在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书法,也表演、传授昆曲,她带出来的四个高足,在促成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“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”一事上,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充和在美国普通地过活,身体情况允许时一直自己做家务,雇不起佣人,也不打算拿自己的本事去市场多赚点银子。它们依然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爱好,从不讨好。可一不留神,就让别人惊艳,这个艳是“无丝毫纤尘”的清雅之艳,更可贵的是她自己无知无觉,毫不在意。充和一直说她没有特别远大的抱负,只是从叔祖母放生、不收特别贫困人家的税赋、收养残疾婴儿等善行中学会慈悲为怀。她的梦想很简单,希望能有一个园子,坐落在溪水边,园子里种着树,她的朋友们随时来做客,“谈笑有鸿儒,往来无白丁”,大家一起做着文学艺术的梦。在美国,她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心目中的小世界,住宅后面她种了一片竹林,也种了牡丹、玫瑰,还种了长葱、葫芦、黄瓜和一棵梨树。她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玩味着她的最爱,也在这样的环境里平静地老去。龙应台曾经给她儿子写信说:“人生像一条从宽阔平原走进森林的路。在平原上可结伙而行,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;一旦进入森林,草丛和荆棘挡路,情形就变了,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。那推推挤挤、同唱同乐的群体情感,那无忧无虑、无猜无忌的同僚深情,在人的一生之中也只有少年有。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,路可能愈走愈孤独。到了熟透的年龄,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,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。”如果我们能够学会自己和自己玩,就有可能像充和老先生一样,耐得起这人生的寂寞。 声明:本文属“纯棉系”原创作品,如须转载请回复“转载”联系授权。 作者 江泓:作家,高级编辑,资深电视媒体人,中国科技大学硕士生导师,白癜风怎么治疗北京最好白癜风医院哪家好